托普卡帕的《史集》:蒙古史由此而生
土耳其共和国的伊斯坦布尔是原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连接欧亚的伊斯坦布尔海峡已披上落日的余晖。老街道一旁的托普卡帕宫殿便是奥斯曼帝国的旧皇宫,这里总有大量的游客云集。然而在宫殿的一角有一座石筑的图书馆却无人问津,只是静静地伫立着。那里沉睡着奥斯曼帝国在六百年间搜集的各种书籍与旧抄本。研究蒙古历史所需要的最基础、最古老也是最好的史料抄本亦包括在其中。
![]() 托普卡帕宫殿
托普卡帕宫殿
《史集》: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史书
拉施特主持编纂的、用波斯语写就的《史集》可以说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史书。它是在位于现今伊朗的蒙古政权旭烈兀兀鲁思(俗称伊儿汗国)政权期间完成的。
公元1295年,第七代伊儿汗合赞通过军事政变夺权上台,改信伊斯兰教,并对国家进行彻底改造,推行了行政改革。为了推行改革,他任命自己的御医拉施特为维齐尔(即宰相)。拉施特出生于伊朗西部的哈马丹,有人认为他实际上是犹太人。合赞和拉施特这对主仆为了重振旭烈兀兀鲁思,一边合力推行改革,一边着手编纂蒙古帝国的历史。
修史的目的有很多。从成吉思汗起家以来已经过去了九十年左右,蒙古已经发展成为横跨欧亚大陆东西、实至名归的世界帝国。但是蒙古人——尤其是在“大西征”中同旭烈兀一起来到“伊朗之地”并定居在此的蒙古人——开始逐渐遗忘自己的来源和历史: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为什么会在“伊朗之地”生活,我们与东方的宗主国“大元兀鲁思”以及其他的汗国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有怎样的血脉联系?合赞从心底尊敬着忽必烈(忽必烈在合赞即位的前一年驾崩),并希望自己能以忽必烈建造的“大元兀鲁思”为蓝本,也像他那样创造出强大坚固的国家和政权。怀抱着这样一种热情,合赞希望能够唤醒所有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蒙古共同体”成员心中对蒙古的认同感。他特别希望居住在伊朗的自己的臣民们能够了解到他们自己所享受的光荣和富贵直接源于旭烈兀、源于他们所连接的蒙古血脉。
合赞希望拉施特编纂的是一部能够起到这样作用的蒙古史。所以《史集》中强烈地反映出了合赞个人的政治立场和见解。合赞不仅仅是修史的号令者,还参与了其中一半以上篇幅的写作和编辑工作。
![]() 身穿搭护的旭烈兀和脱古思可敦
身穿搭护的旭烈兀和脱古思可敦
在《史集》的编纂过程中,他们也参考了蒙古皇室共有的“Altan Tebder”(即蒙古语的《金柜秘册》)等秘藏史料。除此之外,从蒙古本土派往伊朗的孛罗丞相等许多人也为编纂过程提供了信息。蒙古各部代代相传的“旧辞”和族谱等口头和书面的史料都被运用到《史集》的编写中。尽管如此,据拉施特记载,其中核心部分许多内容还是以熟知蒙古诸事及秘史的合赞的口述为基础写就的。
负责编纂的拉施特并没有将编写工作往下委派给编纂人员,而是在处理繁重政务的同时,亲自彻夜编纂。有时在骑马移动的马背上,他也会进行反复的推敲。可以说为了不负主公的厚望,他惜时如金,每时每刻都在努力。
主公的心思:为何要编纂一部帝国史?
但是合赞并没能亲眼看到《史集》完成。1304年,合赞在繁重政务的压力下英年早逝,时年三十四岁。合赞死后,他的弟弟完者都即位,《史集》便被呈献给了完者都。当时这部蒙古史被称为《合赞历史》或《被赞赏的合赞史》(伊斯坦布尔藏本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名为《合赞历史》,其他的抄本名中“被赞赏”一词表达了对已过世合赞的敬意)。
事实上,当我们静下来分析当时的情势就能发现,合赞下令编纂蒙古史(“合赞的蒙古史”一称可能更为准确)的时候,旭烈兀兀鲁思这个游牧民联合体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当时旭烈兀兀鲁思的国库基本是空的,维系游牧骑士军团的经济能力和国家财政面临枯竭。自从1260年创始人旭烈兀带领西征军来到“伊朗之地”正式建立政权以来,兀鲁思一直没有确定的国家机构,而是被放任自由发展,国家内部反复出现内乱。这些问题就这样被抛给了新汗合赞。在这一关系兀鲁思存亡的紧要关头,合赞为了唤醒原先部族联合的“记忆”,展开了“修史事业”。因此合赞修史并不是单纯基于文化角度的考量,而是非做不可,是客观形势的需求。或者说,合赞正是在这种形势的客观影响下才开始修史的。从这个方面来看,这次修史是政治色彩相当浓厚的“国家政策”。
除此之外,合赞还有一个秘密的小心思。从他的立场来看,在他之前的旭烈兀兀鲁思的王位继承都是极为混乱的。合赞的亲生祖父阿八哈(第二代伊儿汗)和父亲阿鲁浑(第四代伊儿汗)死后,其各自的王弟继位,传承王统。至于合赞通过兵变打败的拜都(第六代伊儿汗)则完全是非嫡系的远支旁系。合赞宣扬旭烈兀——阿八哈——阿鲁浑——合赞一脉相承的嫡长子继承是旭烈兀兀鲁斯的正统。他也是据此来指导“旭烈兀兀鲁思”部分的历史编纂的。因此他主张自己并非武装兵变的篡位者,而原本就是正统的继承人。而且只有通过“嫡统”继承的自己如今推行的国家改革,才能够实现旭烈兀兀鲁思的复兴事业。
然而就在合赞去世、修史即将完成时,蒙古帝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激烈的巨大变化。动摇蒙古帝国统治的中亚动乱以海都之死为界,经1303-1304年迅速平静下来,自那之后,蒙古东西一片和谐。欧亚大陆以再次得以统一的蒙古为中心,呈现出舒适祥和之态。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辽阔的和平之地,在这里铺展开来。
帝国的剧变:“蒙古史”也是“世界史”
在蒙古人眼里,世界已经被掌握在自己手中。当他们看到帝国与整个世界的巨大变动时,第八代伊儿汗完者都在既有的“蒙古史”基础上,又下令追加编纂当时世界上主要“种族”的历史,修史的任务被再次交给了拉施特。拉施特在合赞去世后依然担任着旭烈兀兀鲁思的宰相之职,他不仅将当地学者加入编纂队伍,还将中国和克什米尔等地的佛僧、基督徒、犹太学者等集中起来,一起进行史书的编纂。
这次编修的史书可谓包罗万象:从人类祖先亚当开始的希伯来预言者们以及古犹太的历史、古波斯的王朝史、从预言者穆罕默德开始的哈里发们的历史、被蒙古消灭的从花剌子模王朝到伊斯玛仪教团的伊斯兰各王朝史、从传说中的乌古斯汗开始的突厥历史,还有从传说中的人类祖先“盘古”到南宋最后一位少主的中国各王朝史以及以“法兰克”为名的欧洲历史、包含释迦牟尼与佛教历史的印度史,等等。
此后,一部以合赞的“蒙古史”为核心,集合了世界各地区历史的史书问世了。该史书将以蒙古为中心的世界作为出发点——这是自然的——史无前例地将此前的世界历史系统化。另外,在合赞的“蒙古史”和完者都的“世界史”之间,还存在蒙古帝国本身的剧变这一背景,因而这部史书也象征着“世界的世界化”。哈吉来历七百一十年,也就是公元1310到1311年间,这部被呈贡给完者都的增补版“新版史书”,就是《史集》。
《史集》是当时势力极盛的蒙古用波斯语编成的庞大的“蒙古正史”,同时也是14世纪初之前的欧亚各地区的综合史。而且不可忽视的是,它还是一部由合赞和拉施特这两位当事人亲述的、关于旭烈兀兀鲁思及其重组大业的举世无双、完全同步的同时代史。《史集》虽说是用波斯语记载,但事实上夹杂着许多蒙古语、突厥语的用词,甚至还有来源于汉语、藏语、梵语、拉丁语等语言的词语。
若是没有《史集》,蒙古的历史也无从谈起。不仅如此,在欧亚大陆中部展开的突厥—蒙古系游牧民族的历史也很难得以还原,而伊斯兰史、伊朗史也将失去一部意义重大的参考史料。《史集》是人类历史上一部空前的史书,事实上,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视野的开阔性上,以及在最为重要的资料的真实性上,即使在它之后,世界上大概也都没有任何一部史书可以与之匹敌。它不愧是在蒙古这个前无古人的政权与时代背景下诞生的、一部前无古人的庞大的历史书。
另外,它也确切地证明了蒙古当时已经明确意识到了“世界”的存在。到了蒙古时代,人类的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拙作也多次在《史集》的指引下,踏上了穿越时空之旅——去往蒙古及这一人类史上罕见的“时代”的旅程。
哥伦布的梦想:去大汗之国
公元1492年,哥伦布朝着“大汗国”,即忽必烈大汗统治的东方大帝国“大元兀鲁思”,向西开始了他的航海之旅。他的目的地是大元,而非平常人们说的“倭国”或是“印度”,这在他的航海日志的一开头便有明确的说明。
哥伦布出发时,身上还带着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写给遥远的“乞台”大汗的国书(乞台即中国,严格来讲是中国北部。这一名称来源于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时强盛的契丹辽帝国。波斯语中也有Hitai或Hatai的发音,后传至西方)。同时他还带着一本书——依据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这一人物在东方的见闻写成的游记《马可·波罗游记》(又名《寰宇记》,俗称《东方见闻录》)的1485年版。
![]() 西方地理学家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绘制的世界地图
西方地理学家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绘制的世界地图
马可·波罗是谁?
哥伦布当时携带的《马可·波罗游记》以下简称《游记》。——译者注遗留到了今天。在这本书里,随处可见哥伦布所做笔记。尤其是“汗八里”一节,哥伦布在正文左侧空白的地方标注了着重记号,并在偏下的位置记录了“商品不计其数”。“汗八里”指的便是忽必烈的皇都“大都”。
我们今天还不能确定“马可·波罗”这一人物是否真的存在。虽然在威尼斯的图书馆中确实保存有当地资产家马可·波罗的“遗产文书”,但我们并不能保证此“马可·波罗”就是14世纪时周游列国的“马可·波罗”。在当时的意大利北部,有许多姓“波罗”的人家。况且“马可”也不是一个稀有的名字,名叫“马可·波罗”的人必然不会只有一个。
《游记》中许多记录与叙述的真实性,是能够通过其他已经确认的历史文献进行确切验证的。例如关于仅由急行军构成的、可能兼有密探性质的特种部队,《游记》中用很平常的语气提到过这支部队的指挥官的名字。如果不是跟随在忽必烈大汗身边的人,又怎么会知道这种人物的名字呢?关于这名部队指挥官的存在与职务,不久前在某波斯语的年代记和汉语文献中刚刚得到验证。
但是仅凭这些,我们也无法确定“马可·波罗”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关于马可·波罗与其父亲、叔父坐船从印度洋返航的记录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游记》中记录,马可·波罗遵照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命令,护送蒙古公主嫁往旭烈兀兀鲁思所管辖的“伊朗之地”。其中,同行一正两副三名使者的名字与拉施特《史集》的后续史书《瓦撒夫史》中的记录完全一致,而且事情的前后经过也基本相符。唯一不同的是《瓦撒夫史》中并没有提到马可·波罗一家三人。将此书呈献给伊儿汗国的完者都汗时,被授予了 “御前颂词者”的称号。而这部史书也因为名字太长,而参考瓦撒夫的称号,被简称作《瓦撒夫史》,意为“颂词者的历史”。作者本人也被通称作瓦撒夫。)
像这样的例子在《游记》中还有很多。不管记录有多正确、多详细,最重要的“马可·波罗”一行人似乎还是被推到一边,隐于浓雾之中,怎么也捉摸不到——这也是“马可·波罗密探说”,尤其是“马可·波罗是罗马教皇派往东方探查当地情况的密探”等说法的来源。总而言之,像《史集》《元史》等正史的文献中,完全没有记载能够明确地证明《游记》一书中的“马可·波罗”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游记》中经历和见识了种种事情的原型是一定存在的(原型有可能是一个人,也有可能是多个人,不过这并不重要),但是这个人到底是谁、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并不能断定。
欧洲人的东方“记忆”
冠以“马可·波罗游记”之名的抄本有许多版本,并在欧洲各地广泛流传。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游记》是现代的文献研究者、历史研究者从各个版本中选校补订而成的校订本和译注本。虽然研究者都在“情况一定如此”这一设想的前提下整理出一个所谓的“完本”,但是我们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去证明这本书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
马可·波罗本人和他的游记的真实性让人无法看清。但其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在14世纪后半叶之后的欧洲,“马可·波罗”作为一种精神象征是绝对存在的。
哥伦布的船队出发时,忽必烈兴建的帝国“大元兀鲁思”早已不复存在。但借马可·波罗及其一家之名,根据多位欧洲人的所见所闻所汇成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广为流传。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得益于15世纪时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游记》就这样成为最早的一本畅销书。
其中最能够吸引欧洲读者的,大概便是围绕着大都展开的对东方之富的描写了。《游记》不惜笔墨,对东方巨大城市元大都那令人惊异的繁华以及那整齐划一的统制之美,做了精彩又浓重的描写。整本书中最不负《百万之书》一称、用百万这一庞大的计量单位描写最多的也大抵是关于大都的部分《马可·波罗游记》的日译本也称《百万之书》。而马可·波罗由于常用“百万”一词而被称为“百万先生”。——译者注。
在欧亚大陆东西被联结在一起的蒙古时代,东方在蒙古的统治下展现出空前的繁荣。与此相比,欧洲就显得极为微不足道。所以,欧洲人争相阅读《游记》,使“马可·波罗”变得真实起来。即使是蒙古时代已经过去,东方之富的魅力还是一直不断地吸引着欧洲的注意。所以哥伦布也相信了“马可·波罗”的话,带着开拓一条与大汗之国通商道路的信念出发了。憧憬和超越了时空的“记忆”鼓舞着人们去行动。、
![]() 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
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
蒙古记忆推动的新时代
实际上,在忽必烈的大元帝国解体之后,大都也被更名为“北京”,作为明朝的首都继续存在着,但哥伦布却无从得知这一点。但是与此相对,他为欧洲人带去了另一份贵重的礼物。
美洲大陆上的原住民已经独自经营着自己的世界多年,拥有了很长的历史。在欧洲人眼里,资源丰富、面积广阔的美洲大陆就在他们手边,是他们发展的方向。在那之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征服”开始了。欧洲人既是野蛮的,也是幸运的——不,应该说是有些过于幸运了。
当住在欧亚大陆边缘的欧洲人将美洲纳入囊中之后,人类史的发展方向发生了巨大而激烈的转折。“欧洲人的侵略”是与哥伦布的梦想同时开始的。哥伦布最初想开辟到大汗之国的航线,最后却到达了美洲。不过哥伦布本人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还是坚信自己曾到过的那些海岛是大汗之国的一部分。
蒙古将欧亚大陆联结为一个整体,并开辟了自己的时代。关于蒙古的记忆和遗产无论好坏,都继续推动着整个世界向一个整体的新时代前进。历史由一个一个的偶然发展成了不能否定的必然。
巴托尔德一生的挑战:把欧亚大陆内部拉回“世界史”
巴托尔德:讲述欧亚大陆内部的故事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一名伟大的俄国历史学家出现了。他便是巴托尔德。
他以波斯语文献为中心,结合阿拉伯语、突厥语等多种语言的第一手史料,对亚洲历史进行研究,特别是从欧亚大陆内部对其历史进行了认真仔细的重新建构。巴托尔德依靠非凡的能力和学术天赋,进行了常人所不能的努力和钻研。他对在他之前的历史研究认识发起了从其根源开始的怀疑和挑战。
瓦西里·弗拉基米洛维奇·巴托尔德生于1869年,逝于1930年。他几乎将人生的每一天都奉献给了研究。特别是在刚进入20世纪的1901年,他就任圣彼得堡大学教授之后,巴托尔德就把精力全都放在了历史研究上。革命也好,苏联的成立也好,都没有对他的人生产生太大影响。
他的研究可以说是以蒙古时代为中心,这是因为关于蒙古的史料较多,而且蒙古史贯穿了欧亚大陆的古今东西,在重要性上也胜过其他地区和时期的历史。《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便是他的著作之一。这部鸿篇巨制被收录于他的俄语全集之中(共10册),读过的人无不赞叹感喟。
![]() 《蒙古人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
《蒙古人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
得益于他的研究,原本并无确凿依据、缺乏大脉络而难以捕捉的中亚及亚洲内陆地区的历史变得明朗起来。在此之前,人们认为亚洲内陆是不怎么重要的,但是巴托尔德的研究让人们看到,实际上,亚洲内陆与西亚、中东、印度和西北欧亚大陆等“文明圈”的历史紧密相联。读过他的著作的读者都提不出异议,并将他的主张作为严肃的事实而接受,即欧亚大陆的内陆世界也是人类史上如同钥匙一般的重要地区。同时,他也解释了长时间以来所构建的“世界史”到底是怎样一种东西。
19-20世纪地位最高的历史学家
巴托尔德出生时,正值“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亚洲的狂潮。在亚洲内陆勉强度日的游牧民族就如同人类社会的边缘人一般。因此,亚洲内陆和生活在那里的游牧民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也被边缘化了。
这种边缘化的印象在当时的人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使是思想家和理论家也不例外。例如黑格尔、兰克、马克思、斯宾格勒等人对世界和世界史的看法亦不能免俗。他们怀有一种“欧洲是文明世界”的优越感,并没有想去了解欧洲以外的人和事。
但巴托尔德似乎就没有这样的偏见或思维定式。他通过严谨、纯粹的文献研究,证明了这种共通认知是错误且愚蠢的。人们的认识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不,是“应当”发生了变化。
在当时,新的文献和资料不断从亚洲内陆各地出土,在欧洲学界引发了一种热潮。在这些研究者中有俄国的拉德洛夫,还有法国的爱德华·沙畹和他的后继者伯希和等,不乏有数位开创先驱的泰斗级人物。不仅仅是亚洲史研究,从各个领域来说,欧洲的19世纪到20世纪初都是一个巨匠云集的时代。
但若不顾误解而在此直言,巴托尔德才应该是其中地位最高的历史学家,而且明显比其他学者高出一大截。他不仅研究中亚史,还为人类史和世界史梳理出了一条不可或缺的“主心骨”。巴托尔德并没有沾染近代以来以西欧为中心的价值观,使历史群像被等级化,而是将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平等的考量,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叙述一个宏大的故事。
巴托尔德全身心投入到极为朴实的文献研究世界中。我们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一点轻佻浮夸的东西。而且,他的研究为后世留下了巨大的财产。如果没有他的研究,我们现在普遍承认的历史面貌实际上是无法成立的。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但我们都是站在巴托尔德的肩膀上,借助他一生钻研的成果进行历史研究的。
以时代之名:如何再讲蒙古史
13世纪,蒙古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版图。此后到14世纪后半期的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蒙古一直是世界和时代的中心。人类和世界的发展进程自“蒙古时代”开始从根本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蒙古帝国站到了欧亚世界中先后兴起又消亡的各个游牧国家、草原帝国的最高点,而且,在蒙古时代后期,它还取得了农耕世界,并扩展到海洋世界,形成了空前的陆海兼备的巨大国家。以蒙古为中心,欧亚世界首次实现了贯通东西的连接,世界、世界史也从这时开始,形成了一个可以一览无余的整体格局。
当我们思考蒙古帝国之时可以发现,虽然有一件件已知晓的事,但还有很多未解的内容。可以说,很多事实直到今日,即使我们游遍了二十多种语言的多语种原始文献海洋,也有可能找不到其含义而只能继续漂浮其中、等待其被发现。但是,就算我们冲出所有谜团,摆在我们面前最难理解的,还是“时代”。为何人类历史会在此时突然汇聚为一个整体?仿佛之前所有的漫长岁月都是迎接这一“时代”的前奏。同时,在蒙古时代之后可以看到,“时代”在漫长的停滞期中不断下沉,只有在帖木儿王朝大放异彩的中亚地区是唯一的例外,这仿佛也是为新“时代”——“大航海时代”的出现所埋下的巨大伏笔。
关于当时蒙古是否肩负着可以称为“时代的使命”的存在,我们不得而知。但从结果来看,蒙古为人类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无论是在宏观还是微观上,它都为发展至今的世界及其发展过程留下了不可否认的巨大影响。为这个名为“时代”的存在画一幅简单的素描,这便是本书的目的所在。.
![]() (本文为杉山正明《蒙古帝国的兴亡》一书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孙越译、邵建国校。本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授权刊登,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本文为杉山正明《蒙古帝国的兴亡》一书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孙越译、邵建国校。本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授权刊登,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土耳其共和国的伊斯坦布尔是原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连接欧亚的伊斯坦布尔海峡已披上落日的余晖。老街道一旁的托普卡帕宫殿便是奥斯曼帝国的旧皇宫,这里总有大量的游客云集。然而在宫殿的一角有一座石筑的图书馆却无人问津,只是静静地伫立着。那里沉睡着奥斯曼帝国在六百年间搜集的各种书籍与旧抄本。研究蒙古历史所需要的最基础、最古老也是最好的史料抄本亦包括在其中。

《史集》: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史书
拉施特主持编纂的、用波斯语写就的《史集》可以说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史书。它是在位于现今伊朗的蒙古政权旭烈兀兀鲁思(俗称伊儿汗国)政权期间完成的。
公元1295年,第七代伊儿汗合赞通过军事政变夺权上台,改信伊斯兰教,并对国家进行彻底改造,推行了行政改革。为了推行改革,他任命自己的御医拉施特为维齐尔(即宰相)。拉施特出生于伊朗西部的哈马丹,有人认为他实际上是犹太人。合赞和拉施特这对主仆为了重振旭烈兀兀鲁思,一边合力推行改革,一边着手编纂蒙古帝国的历史。
修史的目的有很多。从成吉思汗起家以来已经过去了九十年左右,蒙古已经发展成为横跨欧亚大陆东西、实至名归的世界帝国。但是蒙古人——尤其是在“大西征”中同旭烈兀一起来到“伊朗之地”并定居在此的蒙古人——开始逐渐遗忘自己的来源和历史: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为什么会在“伊朗之地”生活,我们与东方的宗主国“大元兀鲁思”以及其他的汗国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有怎样的血脉联系?合赞从心底尊敬着忽必烈(忽必烈在合赞即位的前一年驾崩),并希望自己能以忽必烈建造的“大元兀鲁思”为蓝本,也像他那样创造出强大坚固的国家和政权。怀抱着这样一种热情,合赞希望能够唤醒所有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蒙古共同体”成员心中对蒙古的认同感。他特别希望居住在伊朗的自己的臣民们能够了解到他们自己所享受的光荣和富贵直接源于旭烈兀、源于他们所连接的蒙古血脉。
合赞希望拉施特编纂的是一部能够起到这样作用的蒙古史。所以《史集》中强烈地反映出了合赞个人的政治立场和见解。合赞不仅仅是修史的号令者,还参与了其中一半以上篇幅的写作和编辑工作。

在《史集》的编纂过程中,他们也参考了蒙古皇室共有的“Altan Tebder”(即蒙古语的《金柜秘册》)等秘藏史料。除此之外,从蒙古本土派往伊朗的孛罗丞相等许多人也为编纂过程提供了信息。蒙古各部代代相传的“旧辞”和族谱等口头和书面的史料都被运用到《史集》的编写中。尽管如此,据拉施特记载,其中核心部分许多内容还是以熟知蒙古诸事及秘史的合赞的口述为基础写就的。
负责编纂的拉施特并没有将编写工作往下委派给编纂人员,而是在处理繁重政务的同时,亲自彻夜编纂。有时在骑马移动的马背上,他也会进行反复的推敲。可以说为了不负主公的厚望,他惜时如金,每时每刻都在努力。
主公的心思:为何要编纂一部帝国史?
但是合赞并没能亲眼看到《史集》完成。1304年,合赞在繁重政务的压力下英年早逝,时年三十四岁。合赞死后,他的弟弟完者都即位,《史集》便被呈献给了完者都。当时这部蒙古史被称为《合赞历史》或《被赞赏的合赞史》(伊斯坦布尔藏本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名为《合赞历史》,其他的抄本名中“被赞赏”一词表达了对已过世合赞的敬意)。
事实上,当我们静下来分析当时的情势就能发现,合赞下令编纂蒙古史(“合赞的蒙古史”一称可能更为准确)的时候,旭烈兀兀鲁思这个游牧民联合体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当时旭烈兀兀鲁思的国库基本是空的,维系游牧骑士军团的经济能力和国家财政面临枯竭。自从1260年创始人旭烈兀带领西征军来到“伊朗之地”正式建立政权以来,兀鲁思一直没有确定的国家机构,而是被放任自由发展,国家内部反复出现内乱。这些问题就这样被抛给了新汗合赞。在这一关系兀鲁思存亡的紧要关头,合赞为了唤醒原先部族联合的“记忆”,展开了“修史事业”。因此合赞修史并不是单纯基于文化角度的考量,而是非做不可,是客观形势的需求。或者说,合赞正是在这种形势的客观影响下才开始修史的。从这个方面来看,这次修史是政治色彩相当浓厚的“国家政策”。
除此之外,合赞还有一个秘密的小心思。从他的立场来看,在他之前的旭烈兀兀鲁思的王位继承都是极为混乱的。合赞的亲生祖父阿八哈(第二代伊儿汗)和父亲阿鲁浑(第四代伊儿汗)死后,其各自的王弟继位,传承王统。至于合赞通过兵变打败的拜都(第六代伊儿汗)则完全是非嫡系的远支旁系。合赞宣扬旭烈兀——阿八哈——阿鲁浑——合赞一脉相承的嫡长子继承是旭烈兀兀鲁斯的正统。他也是据此来指导“旭烈兀兀鲁思”部分的历史编纂的。因此他主张自己并非武装兵变的篡位者,而原本就是正统的继承人。而且只有通过“嫡统”继承的自己如今推行的国家改革,才能够实现旭烈兀兀鲁思的复兴事业。
然而就在合赞去世、修史即将完成时,蒙古帝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激烈的巨大变化。动摇蒙古帝国统治的中亚动乱以海都之死为界,经1303-1304年迅速平静下来,自那之后,蒙古东西一片和谐。欧亚大陆以再次得以统一的蒙古为中心,呈现出舒适祥和之态。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辽阔的和平之地,在这里铺展开来。
帝国的剧变:“蒙古史”也是“世界史”
在蒙古人眼里,世界已经被掌握在自己手中。当他们看到帝国与整个世界的巨大变动时,第八代伊儿汗完者都在既有的“蒙古史”基础上,又下令追加编纂当时世界上主要“种族”的历史,修史的任务被再次交给了拉施特。拉施特在合赞去世后依然担任着旭烈兀兀鲁思的宰相之职,他不仅将当地学者加入编纂队伍,还将中国和克什米尔等地的佛僧、基督徒、犹太学者等集中起来,一起进行史书的编纂。
这次编修的史书可谓包罗万象:从人类祖先亚当开始的希伯来预言者们以及古犹太的历史、古波斯的王朝史、从预言者穆罕默德开始的哈里发们的历史、被蒙古消灭的从花剌子模王朝到伊斯玛仪教团的伊斯兰各王朝史、从传说中的乌古斯汗开始的突厥历史,还有从传说中的人类祖先“盘古”到南宋最后一位少主的中国各王朝史以及以“法兰克”为名的欧洲历史、包含释迦牟尼与佛教历史的印度史,等等。
此后,一部以合赞的“蒙古史”为核心,集合了世界各地区历史的史书问世了。该史书将以蒙古为中心的世界作为出发点——这是自然的——史无前例地将此前的世界历史系统化。另外,在合赞的“蒙古史”和完者都的“世界史”之间,还存在蒙古帝国本身的剧变这一背景,因而这部史书也象征着“世界的世界化”。哈吉来历七百一十年,也就是公元1310到1311年间,这部被呈贡给完者都的增补版“新版史书”,就是《史集》。
《史集》是当时势力极盛的蒙古用波斯语编成的庞大的“蒙古正史”,同时也是14世纪初之前的欧亚各地区的综合史。而且不可忽视的是,它还是一部由合赞和拉施特这两位当事人亲述的、关于旭烈兀兀鲁思及其重组大业的举世无双、完全同步的同时代史。《史集》虽说是用波斯语记载,但事实上夹杂着许多蒙古语、突厥语的用词,甚至还有来源于汉语、藏语、梵语、拉丁语等语言的词语。
若是没有《史集》,蒙古的历史也无从谈起。不仅如此,在欧亚大陆中部展开的突厥—蒙古系游牧民族的历史也很难得以还原,而伊斯兰史、伊朗史也将失去一部意义重大的参考史料。《史集》是人类历史上一部空前的史书,事实上,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视野的开阔性上,以及在最为重要的资料的真实性上,即使在它之后,世界上大概也都没有任何一部史书可以与之匹敌。它不愧是在蒙古这个前无古人的政权与时代背景下诞生的、一部前无古人的庞大的历史书。
另外,它也确切地证明了蒙古当时已经明确意识到了“世界”的存在。到了蒙古时代,人类的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拙作也多次在《史集》的指引下,踏上了穿越时空之旅——去往蒙古及这一人类史上罕见的“时代”的旅程。
哥伦布的梦想:去大汗之国
公元1492年,哥伦布朝着“大汗国”,即忽必烈大汗统治的东方大帝国“大元兀鲁思”,向西开始了他的航海之旅。他的目的地是大元,而非平常人们说的“倭国”或是“印度”,这在他的航海日志的一开头便有明确的说明。
哥伦布出发时,身上还带着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写给遥远的“乞台”大汗的国书(乞台即中国,严格来讲是中国北部。这一名称来源于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时强盛的契丹辽帝国。波斯语中也有Hitai或Hatai的发音,后传至西方)。同时他还带着一本书——依据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这一人物在东方的见闻写成的游记《马可·波罗游记》(又名《寰宇记》,俗称《东方见闻录》)的1485年版。

马可·波罗是谁?
哥伦布当时携带的《马可·波罗游记》以下简称《游记》。——译者注遗留到了今天。在这本书里,随处可见哥伦布所做笔记。尤其是“汗八里”一节,哥伦布在正文左侧空白的地方标注了着重记号,并在偏下的位置记录了“商品不计其数”。“汗八里”指的便是忽必烈的皇都“大都”。
我们今天还不能确定“马可·波罗”这一人物是否真的存在。虽然在威尼斯的图书馆中确实保存有当地资产家马可·波罗的“遗产文书”,但我们并不能保证此“马可·波罗”就是14世纪时周游列国的“马可·波罗”。在当时的意大利北部,有许多姓“波罗”的人家。况且“马可”也不是一个稀有的名字,名叫“马可·波罗”的人必然不会只有一个。
《游记》中许多记录与叙述的真实性,是能够通过其他已经确认的历史文献进行确切验证的。例如关于仅由急行军构成的、可能兼有密探性质的特种部队,《游记》中用很平常的语气提到过这支部队的指挥官的名字。如果不是跟随在忽必烈大汗身边的人,又怎么会知道这种人物的名字呢?关于这名部队指挥官的存在与职务,不久前在某波斯语的年代记和汉语文献中刚刚得到验证。
但是仅凭这些,我们也无法确定“马可·波罗”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关于马可·波罗与其父亲、叔父坐船从印度洋返航的记录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游记》中记录,马可·波罗遵照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命令,护送蒙古公主嫁往旭烈兀兀鲁思所管辖的“伊朗之地”。其中,同行一正两副三名使者的名字与拉施特《史集》的后续史书《瓦撒夫史》中的记录完全一致,而且事情的前后经过也基本相符。唯一不同的是《瓦撒夫史》中并没有提到马可·波罗一家三人。将此书呈献给伊儿汗国的完者都汗时,被授予了 “御前颂词者”的称号。而这部史书也因为名字太长,而参考瓦撒夫的称号,被简称作《瓦撒夫史》,意为“颂词者的历史”。作者本人也被通称作瓦撒夫。)
像这样的例子在《游记》中还有很多。不管记录有多正确、多详细,最重要的“马可·波罗”一行人似乎还是被推到一边,隐于浓雾之中,怎么也捉摸不到——这也是“马可·波罗密探说”,尤其是“马可·波罗是罗马教皇派往东方探查当地情况的密探”等说法的来源。总而言之,像《史集》《元史》等正史的文献中,完全没有记载能够明确地证明《游记》一书中的“马可·波罗”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游记》中经历和见识了种种事情的原型是一定存在的(原型有可能是一个人,也有可能是多个人,不过这并不重要),但是这个人到底是谁、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并不能断定。
欧洲人的东方“记忆”
冠以“马可·波罗游记”之名的抄本有许多版本,并在欧洲各地广泛流传。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游记》是现代的文献研究者、历史研究者从各个版本中选校补订而成的校订本和译注本。虽然研究者都在“情况一定如此”这一设想的前提下整理出一个所谓的“完本”,但是我们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去证明这本书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
马可·波罗本人和他的游记的真实性让人无法看清。但其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在14世纪后半叶之后的欧洲,“马可·波罗”作为一种精神象征是绝对存在的。
哥伦布的船队出发时,忽必烈兴建的帝国“大元兀鲁思”早已不复存在。但借马可·波罗及其一家之名,根据多位欧洲人的所见所闻所汇成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广为流传。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得益于15世纪时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游记》就这样成为最早的一本畅销书。
其中最能够吸引欧洲读者的,大概便是围绕着大都展开的对东方之富的描写了。《游记》不惜笔墨,对东方巨大城市元大都那令人惊异的繁华以及那整齐划一的统制之美,做了精彩又浓重的描写。整本书中最不负《百万之书》一称、用百万这一庞大的计量单位描写最多的也大抵是关于大都的部分《马可·波罗游记》的日译本也称《百万之书》。而马可·波罗由于常用“百万”一词而被称为“百万先生”。——译者注。
在欧亚大陆东西被联结在一起的蒙古时代,东方在蒙古的统治下展现出空前的繁荣。与此相比,欧洲就显得极为微不足道。所以,欧洲人争相阅读《游记》,使“马可·波罗”变得真实起来。即使是蒙古时代已经过去,东方之富的魅力还是一直不断地吸引着欧洲的注意。所以哥伦布也相信了“马可·波罗”的话,带着开拓一条与大汗之国通商道路的信念出发了。憧憬和超越了时空的“记忆”鼓舞着人们去行动。、

蒙古记忆推动的新时代
实际上,在忽必烈的大元帝国解体之后,大都也被更名为“北京”,作为明朝的首都继续存在着,但哥伦布却无从得知这一点。但是与此相对,他为欧洲人带去了另一份贵重的礼物。
美洲大陆上的原住民已经独自经营着自己的世界多年,拥有了很长的历史。在欧洲人眼里,资源丰富、面积广阔的美洲大陆就在他们手边,是他们发展的方向。在那之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征服”开始了。欧洲人既是野蛮的,也是幸运的——不,应该说是有些过于幸运了。
当住在欧亚大陆边缘的欧洲人将美洲纳入囊中之后,人类史的发展方向发生了巨大而激烈的转折。“欧洲人的侵略”是与哥伦布的梦想同时开始的。哥伦布最初想开辟到大汗之国的航线,最后却到达了美洲。不过哥伦布本人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还是坚信自己曾到过的那些海岛是大汗之国的一部分。
蒙古将欧亚大陆联结为一个整体,并开辟了自己的时代。关于蒙古的记忆和遗产无论好坏,都继续推动着整个世界向一个整体的新时代前进。历史由一个一个的偶然发展成了不能否定的必然。
巴托尔德一生的挑战:把欧亚大陆内部拉回“世界史”
巴托尔德:讲述欧亚大陆内部的故事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一名伟大的俄国历史学家出现了。他便是巴托尔德。
他以波斯语文献为中心,结合阿拉伯语、突厥语等多种语言的第一手史料,对亚洲历史进行研究,特别是从欧亚大陆内部对其历史进行了认真仔细的重新建构。巴托尔德依靠非凡的能力和学术天赋,进行了常人所不能的努力和钻研。他对在他之前的历史研究认识发起了从其根源开始的怀疑和挑战。
瓦西里·弗拉基米洛维奇·巴托尔德生于1869年,逝于1930年。他几乎将人生的每一天都奉献给了研究。特别是在刚进入20世纪的1901年,他就任圣彼得堡大学教授之后,巴托尔德就把精力全都放在了历史研究上。革命也好,苏联的成立也好,都没有对他的人生产生太大影响。
他的研究可以说是以蒙古时代为中心,这是因为关于蒙古的史料较多,而且蒙古史贯穿了欧亚大陆的古今东西,在重要性上也胜过其他地区和时期的历史。《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便是他的著作之一。这部鸿篇巨制被收录于他的俄语全集之中(共10册),读过的人无不赞叹感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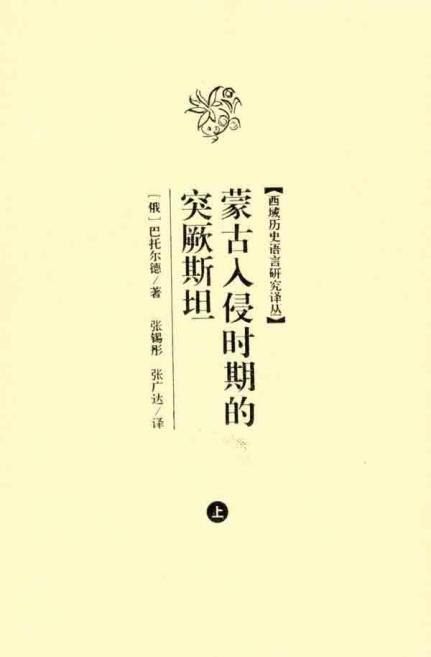
得益于他的研究,原本并无确凿依据、缺乏大脉络而难以捕捉的中亚及亚洲内陆地区的历史变得明朗起来。在此之前,人们认为亚洲内陆是不怎么重要的,但是巴托尔德的研究让人们看到,实际上,亚洲内陆与西亚、中东、印度和西北欧亚大陆等“文明圈”的历史紧密相联。读过他的著作的读者都提不出异议,并将他的主张作为严肃的事实而接受,即欧亚大陆的内陆世界也是人类史上如同钥匙一般的重要地区。同时,他也解释了长时间以来所构建的“世界史”到底是怎样一种东西。
19-20世纪地位最高的历史学家
巴托尔德出生时,正值“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亚洲的狂潮。在亚洲内陆勉强度日的游牧民族就如同人类社会的边缘人一般。因此,亚洲内陆和生活在那里的游牧民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也被边缘化了。
这种边缘化的印象在当时的人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使是思想家和理论家也不例外。例如黑格尔、兰克、马克思、斯宾格勒等人对世界和世界史的看法亦不能免俗。他们怀有一种“欧洲是文明世界”的优越感,并没有想去了解欧洲以外的人和事。
但巴托尔德似乎就没有这样的偏见或思维定式。他通过严谨、纯粹的文献研究,证明了这种共通认知是错误且愚蠢的。人们的认识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不,是“应当”发生了变化。
在当时,新的文献和资料不断从亚洲内陆各地出土,在欧洲学界引发了一种热潮。在这些研究者中有俄国的拉德洛夫,还有法国的爱德华·沙畹和他的后继者伯希和等,不乏有数位开创先驱的泰斗级人物。不仅仅是亚洲史研究,从各个领域来说,欧洲的19世纪到20世纪初都是一个巨匠云集的时代。
但若不顾误解而在此直言,巴托尔德才应该是其中地位最高的历史学家,而且明显比其他学者高出一大截。他不仅研究中亚史,还为人类史和世界史梳理出了一条不可或缺的“主心骨”。巴托尔德并没有沾染近代以来以西欧为中心的价值观,使历史群像被等级化,而是将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平等的考量,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叙述一个宏大的故事。
巴托尔德全身心投入到极为朴实的文献研究世界中。我们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一点轻佻浮夸的东西。而且,他的研究为后世留下了巨大的财产。如果没有他的研究,我们现在普遍承认的历史面貌实际上是无法成立的。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但我们都是站在巴托尔德的肩膀上,借助他一生钻研的成果进行历史研究的。
以时代之名:如何再讲蒙古史
13世纪,蒙古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版图。此后到14世纪后半期的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蒙古一直是世界和时代的中心。人类和世界的发展进程自“蒙古时代”开始从根本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蒙古帝国站到了欧亚世界中先后兴起又消亡的各个游牧国家、草原帝国的最高点,而且,在蒙古时代后期,它还取得了农耕世界,并扩展到海洋世界,形成了空前的陆海兼备的巨大国家。以蒙古为中心,欧亚世界首次实现了贯通东西的连接,世界、世界史也从这时开始,形成了一个可以一览无余的整体格局。
当我们思考蒙古帝国之时可以发现,虽然有一件件已知晓的事,但还有很多未解的内容。可以说,很多事实直到今日,即使我们游遍了二十多种语言的多语种原始文献海洋,也有可能找不到其含义而只能继续漂浮其中、等待其被发现。但是,就算我们冲出所有谜团,摆在我们面前最难理解的,还是“时代”。为何人类历史会在此时突然汇聚为一个整体?仿佛之前所有的漫长岁月都是迎接这一“时代”的前奏。同时,在蒙古时代之后可以看到,“时代”在漫长的停滞期中不断下沉,只有在帖木儿王朝大放异彩的中亚地区是唯一的例外,这仿佛也是为新“时代”——“大航海时代”的出现所埋下的巨大伏笔。
关于当时蒙古是否肩负着可以称为“时代的使命”的存在,我们不得而知。但从结果来看,蒙古为人类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无论是在宏观还是微观上,它都为发展至今的世界及其发展过程留下了不可否认的巨大影响。为这个名为“时代”的存在画一幅简单的素描,这便是本书的目的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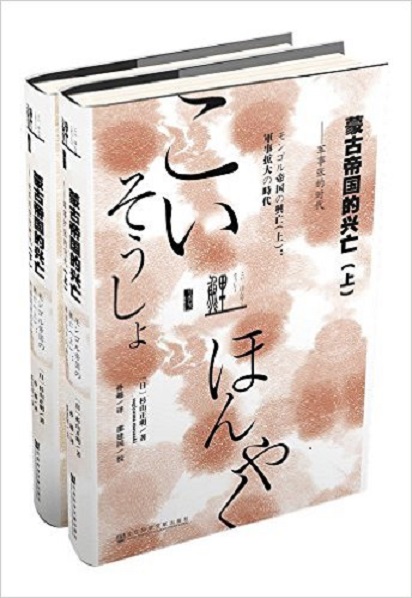
录入编辑:于淑娟
